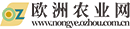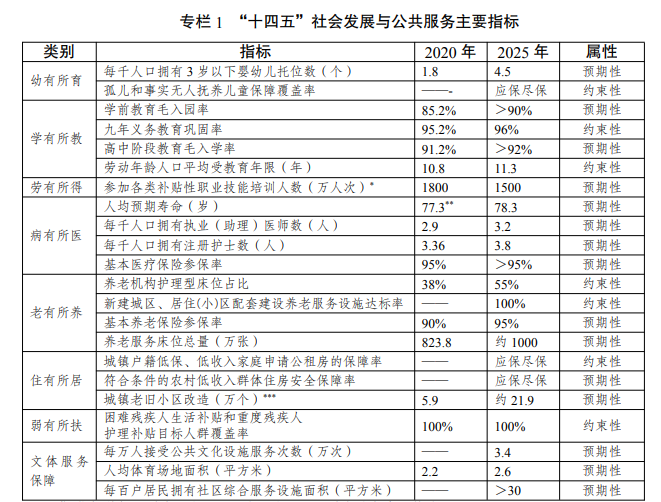(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本期人物 · 马啸
编者按:
基础设施投资是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如何自下而上地争取政策资源?官僚决策体系中碎片化的权力结构如何发挥作用?青年学者马啸的博士论文以中国的高铁建设项目为切入点,为我们展示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政治行动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之间如何互相影响。该博士论文也于2022年6月份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Localized Bargain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Program(《地方化博弈:中国高铁项目的政治经济学》),引发学界关注。本期“学人专访”,我们有幸邀请到马啸老师,带领我们从人性出发,在田野中丰富意义,探索政治的奥秘。让我们跟随老师,一起发展接地气的发展政治学!
(专访现场:马啸老师对“政治学人”读者的寄语)
政治学人:马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政治学人》的专访!首先恭喜您的专著Localized Bargain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Program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对您而言,博士论文出版成书意味着什么?成书期间有令您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吗?可以向正在计划将自己博士论文成书出版的青年学者分享一些经验吗?
马啸:
在我读硕士期间,有位研究日本近代史的老师,他通过与福柯等学者的对话撰写了关于日本明治时期犯罪惩罚制度的专著。当时他的书刚刚出版,我和这位老师交流,问他自己的书出版了是否很开心,结果他说他终于有个机会可以这辈子再也不用去碰这个话题了。我对他的回答感到很吃惊,但也能理解,因为算上读博士的时间,他大概花了10年的时间对这个话题进行研究、修改和打磨,可能已经产生了疲惫感。我觉得博士论文出版成书的第一个意义,可能就是对之前7-9年做的研究有了一个交代,而且是以内部逻辑较为连贯的成果的形式最终出版。虽然现在社会科学的主流可能还是以发论文为主,很多著作也可能是多篇论文的合集,但我觉得能像书籍这样用逻辑连贯的方式把一个话题讲清楚是一个比较难得的机会。
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一个感想,就是写作其实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撰写一篇论文已经很不容易,更何况是写一本篇幅大概相当于五六篇论文的书,甚至痛苦程度可能还不止成比例放大五六倍。在写作过程中,我采取了很多办法来督促我坚持写下去,包括我每天早上会跟同事说好今天需要完成的目标,然后请同事来帮忙监督。我当时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我不是用自己的母语在写作,所以才会有比较痛苦的写作经历。后来我请教了博士就读期间的老师,她与我有相同的困惑,说每次她要在电脑上开始创作时,就会觉得写作是一个需要克服很大心理障碍的过程,因此宁肯去做诸如邮件解答学生的问题等相对轻松的工作。所以无论语言,把自己的思维整理成上下逻辑连贯缜密的文字,是一件需要做好相当大心理准备的事情。回过头来看这些经历,对我自己的启发是:无论处于怎样一个过程,如果一天中能写上几百字的话,最终都会对完成写作有很大的帮助。即使一开始不成熟,之后可以回过头去完善修改,比因为惧怕写作而不断拖延肯定要好。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锻炼写作能力的很好的实践。
政治学人:您曾提到政治学研究应当“从一个微观的、每个人都能有切身感受的视角,逐步上升到国家和国际政治”。从中国高铁建设项目着手研究地方政府博弈正体现了您的微观关切。是何种契机促使您找到如此有趣的切入点?您认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应从何处着手?
马啸:
我从大学阶段起就对铁路非常感兴趣。由于本科学习日语,我在日本交换学习了一年。期间我看到日本铁路网的发达程度、对于不同区域的渗透程度都高于当时的中国。在日本,很多人坐火车上下班。在2008、2009年时,中国仅少数大城市有地铁,人们坐火车上下班通勤的情况也较为少见。当时我心里就在想:像日本这种便捷的交通形式,是否有一天可能会来到中国。恰巧在2008、2009年的时候,中国最早的几条高铁通车。2008年奥运会时,京津城际铁路通车;2009年,第一条长距离高铁——武汉到广州的武广高铁通车。国内高铁的通车,使当时正在国外学习的我感到很神奇,开始设想中国将来是否有人会坐铁路上下班。这是我作为一位普通铁路爱好者的兴趣发端,但在当时并未上升到学术问题。
马啸老师专著:《地方化博弈:中国高铁项目的政治经济学》
后来在我博士论文开题,即2014、2015年之时,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的高铁站,高铁网络扩张到三四线城市。在进入到三四线城市后,具体在哪个城市设高铁站存在很多博弈的空间。2015年5月便出现过一个围绕铁路设站的大争议:广安是四川的一个地级市,高铁在经过广安时是经过广安市还是广安市旁边的邻水和大竹县?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博弈空间。当时各个地方涌现出很多要求设立高铁站的方式,包括网上发帖、政府主动出面(如带队到北京争取设立高铁站)、民间自发组织写横幅和签字,甚至上街请愿。类似事件被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我也受到了这些现象的启发,觉得似乎能将我的个人兴趣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以及国家—社会关系中的一些问题连接起来,进而成为一个比较理想的博士论文选题。毕竟一个题目从选定之时开始到后面发表要花将近七八年的时间,选择自己真心感兴趣的问题很重要。
在具体的研究问题上,我觉得论文的问题既需要聚焦,又可以延伸。我的博士论文后来在成书时,单独有一章论述本书的发现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特别是研究发现在增进我们对中国政治经济了解之外,对政治学的一般理论有什么贡献:这个背后的故事可以和政治经济学中的分配政治进行对话、可以和官僚政治进行对话、也可以和国家—社会关系的经典理论进行对话。在书中,我主动告诉了读者本书的发现能与前述内容产生联系。但问题聚焦的现象本身,即地方如何尝试获得高铁投资这一问题不会改变,只是围绕这个问题会有不同切入点。
政治学人:您于《在田野中丰富意义:以府际政策博弈研究为例》一文中提及,“进入田野,接受经验世界的信息冲击,思考现实与理论假设之间的张力,能够为理论建构注入新的洞见和活力”。在田野调查中的经历也最终成为您博士论文的一个章节。可否以您的博士论文为例,简单和我们聊聊如何在田野中探求人性,丰富研究意义?以及您如何看待进入田野这一过程?
马啸:
在我所做的中国政策过程的研究中,田野调查是必要的。中国的政策过程与官僚政治涉及的许多重要概念的源起都受田野调查的启发,例如荣敬本、杨雪冬老师他们所提的很有影响力的“压力型体制”的概念,就是基层调研的一个产物。其实很多在中国政治中耳熟能详的概念,都是学者经过长期观察所得到的结果。
政治学涉及到政府这一主体,所以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与官员打交道,这也经常成为一大难点。对此,我们领域内已经积累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例如研究者需要增强自身专业素养,在与官员互动时主动介绍自己职业的要求标准和研究的相关信息等内容。另外,研究者可以尝试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与调查对象建立更深的联系,尽量找到与后者的共同点,使之产生共情,而非仅仅通过第三方介绍来进行交流。我在做这篇论文的田野调查时,与大多数接触的官员都会在认识后进行第二次访谈(回访)。一般而言,在调查中如果对方愿意进行第二次访谈,那么就表明“我”和对方之间的关系已经比原先通过第三方介绍的两个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同时,在对方工作之外的交流对田野调查而言也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者应该耐心对待访谈,认真准备访谈问题,抓取有效信息,并以最低标准和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所谓最低标准即不违法和尽量不给他人的供走生活造成负面影响。在政治学的田野调查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护研究对象的隐私。在这一基本要求之外,研究者还要充分把握访谈问题和访谈对象的工作内容。如果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的话语能够超出访谈对象的设想,使访谈对象觉得研究者对自身工作领域所知多于之前的预设,那么人的天性就会多少驱使访谈对象更多的表达。现在不少知名高校的学生进行访谈,在面对他们的访谈时,访谈对象虽然可能会受到有些东西不能讲等诸多限制,但由于知名高校学生这一身份,访谈对象至少会愿意谈及一些自己认为对研究者有帮助的内容。这也是前面提到的“访谈者效应”的一个体现。所以,我认为事先做好一些调研工作和背景调查,对访谈对象的工作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获得较高质量访谈结果有决定性影响。
我对进入田野这个过程有两个看法。一方面,政治学的田野调查不完全等同于其它学科的田野调查。社会科学的意义在于重新组织经验事实,然后形成理论。如果仅仅只是描述、记录事实,那可能是其它某些学科所做的事情,比如历史学就需要重新发现、阐释史料。政治学的田野调查一方面要通过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来全身心进入田野,把自己变成研究对象中的一部分,以此发掘更多事实。这要求研究者对信息保持一种敏感态度,要善于将收集到的信息重新组织起来。另一方面,研究者也要跳出田野,否则可能会忽视事实之间的一些联系,不能意识到研究真正想要捕捉的问题。这要求研究者具有一定的抽象思考和提炼规律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恰恰和上面提到的收集信息能力存在一些张力。所以,进入田野和跳出田野对研究者而言都是需要的,需要找到一个好的平衡。
政治学人:高铁建设项目背后的政治博弈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发展政治学正是由这三个学科交叉所产生的一个政治学领域。您在《发展中的发展政治学》一文指出,发展政治学的研究议题和话语体系会受到不同时期现实政治的影响,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使发展政治学更富时代特色?
马啸:
谢谢你的问题。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需要人们刻意去挖掘。社会科学是基于现实的研究,所以多少会带有时代特色。正是因为现实中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人们才会去研究。比如六七十年代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出现的对世界体系的研究,这是在原殖民地独立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基于当时许多殖民地独立的背景,人们发现虽然新的民族国家成立了,但他们之间的经济权力关系依旧不平等,为什么这种不平等继续存在,就成了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殖民地国家独立后,还面临要建立一套新的国家体系、选择何种发展道路的现实。这些现实世界的需求,推动了我们后来看到了发展政治学领域包括现代化理论在内的一系列的研究的出现,非常富有时代特色。又比如,过去三十年间,比较政治学领域的民主化研究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直接原因是现实世界发生了这些变化,这也是基于苏东剧变等“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政治现实。
最近几十年,我们生活在相对比较稳定的时代,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现实世界并未发生非常大的变革。相比二战结束、殖民地独立、大规模的地区战争和动乱频发的五六十年代,我们作为普通人是幸运的,但作为政治学者,逐渐和一些重要的话题梳离。现在的政治学不再积极地回答例如民主、权威、国家、冲突等经典的理论议题,而是尝试回答一些国家治理中的相对更微观的问题。中文论文中已经有很多关于政治学公管化的讨论,其实这种现象在中国之外的政治学研究中也存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对我们这个相对和平稳定年代的现实反映。中国有句话叫“国家不幸诗家幸”,就体现了这个逻辑。
所以,我认为时代特色不需要我们特意地发掘,它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在每一代学者的研究之中。但如果说非要发掘当下所处时代的新话题的话,可能我们也正处于巨变的前沿。诸如目前将一些信息技术应用到公共治理的特定环节,以及近两年人工智能的发展等,可能我们正处在类似蒸汽机刚被发明的时代。但在蒸汽机出现的时代,当时的人们也并不会意识到蒸汽机将会给未来世界带来怎样大的变化,它的影响更多是后人以后视镜的视角总结的。而我们今天可能也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只是可能需要要在20年,甚至50年后,才会意识到现在这个变化时代的深刻影响。
政治学人:从专著确定出版开始,就引发学界关注与讨论,您也收到多个关于此书的专访和讲座邀请。在关于本书的学术交流中,您收到过哪些有启发意义的探讨?其他学者有什么代表性困惑吗?您有希望进一步阐释或回应的问题吗?
马啸:
我在书里提出了一个叫“地方化博弈”的理论框架,即地方政府为了获取更多资源,会采取“跑部钱进”、发动群众等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措施来向上博弈。书中主要以高铁建设中的博弈展开论证,但地方化博弈的现象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存在,比如其它类型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地铁、港口等)的落地,经济特区的设置,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所以经常会有人问我为什么只关注高铁,为什么只用了高铁的案例来展示地方化博弈?我对此的回答是:2005年之前,中国没有高铁;而从2005年到现在,高铁建设迅速的在中国各个省市铺开。这为我提供了足够多的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可以供我们在个案之外做更系统性的分析。另外,就像前面提到的,我在选题过程中也考虑了个人兴趣。
当然个人兴趣只是一个方面,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最终能否写出一篇被所在学科接受和认可的学术论文。以我所在的政治经济学或发展政治学领域而言,博士论文最终还是需要以一项较为扎实的实证研究的形式呈现。我这里说的实证研究,更多指向需要大样本分析的定量研究和因果关系识别设计。如果去研究其它的一些政策领域,就不太会有像高铁这样提供丰富差异性的数据。某一政策的决定(例如行政区划的变动),可能一年就发生了一次或者几次,一次可能就涉及几个城市,这对更为系统的实证研究来说观察数量来说是不太够的。而如果只是依赖个案研究,在发表上就可能会面临一些困境。但在全国铺开建设的高铁,在两千八百多个县、三百多个地级市里产生了非常丰富的时空差异性,能提供一个进行统计分析的空间。所以最初选题的时候,也是结合了个人兴趣和学科发表要求等多个考量。这是我对为什么在书中主要关注高铁这个问题作出的回应,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其它政策领域不存在类似的地方化博弈;相反,这种政策博弈动态存在于相当多的领域,将来应该被更好的发掘。
政治学人:您在之前的访谈中提到正在开展一些新研究,意图通过新研究进一步验证专著的理论框架。能否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些新研究,或者分享下最新的研究发现?
马啸:
我现在主要在做两类研究。第一类和书中所提到的地方化博弈框架有关,即地方如何利用不同的策略会向上争取资源。对于这个框架,就像你刚才说的,其他学者也提出了疑问:它是否只适用于高铁这一个领域?现在我和我的合作者正尝试观察其它类型的政策资源中是否存在类似规律,如地铁的审批、港口资源的集中管理。这些研究其实更多是对之前的框架进行验证。第二类则是一个新的议题,就是现在的干部管理体制或干部激励机制会产生何种意想不到的结果。现在考核的本质目的是希望官员能够按照组织和上级的目标认真工作,但很多的考核最终可能会扭曲官员的行为,导致产生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因此,我想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去观察,为什么考核机制在某些领域内能使官员很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和自身能动性,但在某些领域却会对治理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我可能会选择几个政策领域进行比较,做一些实证研究。这是我目前正在考虑的未来要做的一个大项目。
政治学人: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政治学应植根于寻常生活之中,植根于人性”,您认为青年政治学人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应如何从人性出发,做接地气的政治学?可以借“政治学人”平台为大家送上一些寄语吗?
马啸:
我希望同学们未来从事的研究可以做到“顶天立地”。我先从“立地”说起。“立地”是大家要尽量多接触自己的研究对象,不能只从文献、媒体等二手渠道中了解,要多到一线去接触。有了接触以后,才能在研究中提供更多有趣的视角和证据,才能让你的读者感受到你是一位对你的研究对象有很深刻认知的学者。我们现在常说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对从事研究的人来说,就是要扎根到一线,在现实之中去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而“顶天”则是在获取一手资料、了解研究对象之外,社会科学工作者或者政治学学者还需要从纷繁复杂的现实经验材料之中,提炼并抽象出一般规律,做到同经典理论对话,获得超出单个案例甚至单个国家经验的普遍性规律。
“顶天”与“立地”看似有一定矛盾,但其实是有机结合的两方面。如果没有很丰富的一手的现实经验材料,理论往往很空洞;如果只有理论而没有实证,研究往往只是空中楼阁。同时社会科学是一个以理论和概念来界定自己学术身份的学科,所以如果只有实证或现实的经验而缺乏对理论的抽象,那也不是一项很出彩的社会科学研究。
马啸老师与采访者欧阳星、李健、王馨瑶的合影
点击下方标题,查看更多学人专访
解锁政治学研究的制度奥秘——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海归教师马啸
更多精彩文章回顾
■ 学人专访采编集锦:
包刚升|曹海军|陈超|陈周旺|段德敏|房宁|费海汀|耿曙|郭台辉|郭忠华|郭道久|郭定平|黄琪轩|季乃礼|金安平|荆学民|郎友兴|李春福|李辉|李路曲|李石|吕德文|刘建军|刘伟|马得勇|欧阳静|孙磊|唐世平|佟德志|汪段泳|王立峰|王正绪|吴冠军|吴晓林|肖晞|谢岳|徐勇|徐湘林|郇庆治|熊易寒|杨光斌|杨雪冬|杨阳|殷冬水|颜德如|游宇|张星久|周平|朱光磊|朱天飚|张国清|张树华|张贤明
■青年学人访谈集锦:
陈科霖|陈青霞|黄晨|季程远|刘九勇|向杨|张力伟
■ 特色访谈栏目集锦:
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山大学|阿富汗田野调查|俄乌冲突评议|六周年访谈|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化
■编译与转载之集锦:
陈国权|李强|任剑涛|桑玉成|唐士其|王绍光|项飙|俞可平|周振鹤|朱光磊|阿里夫·德里克|埃里克·沃格林|安东尼·吉登斯|道格拉斯·凯尔纳|菲利普·佩蒂特|弗朗西斯·福山(上)|弗朗西斯·福山(下)|哈维·曼斯菲尔德|克劳斯·泽格伯斯|克里斯托夫·贾弗雷洛|昆廷·斯金纳|罗伯特·达尔|马克·里拉|马啸|迈克尔·桑德尔|乔尔·米格代尔|斯拉沃热·齐泽克|西达·斯考切波|希尔·斯坦纳|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约翰·米尔斯海默|威尔・金里卡
采 编|史清渠 沈 琰
采 访|欧阳星 李 健 王馨瑶
编辑|宁豪龙 代昌敏 沈 琰
海 报|代昌敏
初 审|史清渠
终 审|大 兰 欧阳星
本文核心内容系政治学人平台首发,文章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立场;个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及网站链接;媒体转载(包括网站、微博、微信号)请联系政治学人微信后台。识别二维码可添加编辑团队微信。